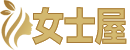當(dāng)代中國家庭教育現(xiàn)狀 劉慶邦長篇小說《家長》:新世紀(jì)中國“家庭教育問題小說”的審美書寫
百年來,教育問題是中國現(xiàn)代社會轉(zhuǎn)型中的核心問題。“教育救國”是很多知識分子、教育工作者的理想與追求。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,尤其是“教育問題小說”,是一個很重要的創(chuàng)作領(lǐng)域。葉圣陶的教育小說就是很典型的審美創(chuàng)作,其《潘先生在難中》《倪煥之》等是影響巨大的文學(xué)名篇。新世紀(jì)以來,隨著中國社會的大發(fā)展,大眾教育的普及,民眾對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訴求越來越強(qiáng)烈。教育問題極為凸顯,家長、教師、孩子都處于極度的焦慮之中。作為“底層寫作”的一位當(dāng)代著名作家,劉慶邦始終以細(xì)致入微的觀察、充滿人文關(guān)懷的筆觸,書寫著底層大眾群體的凡人俗事。作家的生活經(jīng)歷與生存體驗為其創(chuàng)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,劉慶邦亦是如此——他來自農(nóng)村,又有著九年的礦工經(jīng)歷。農(nóng)民與礦工這兩大群體是劉慶邦小說的重要表現(xiàn)對象。他關(guān)注這兩大群體的心靈世界,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我用掘巷道的方法,在向人情、人性和人的心靈深處掘進(jìn)。”發(fā)表于《十月·長篇小說》2019年第1期的《家長》,浸透著劉慶邦對于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心靈世界的深切關(guān)懷。劉慶邦這次把目光投向教育問題,通過書寫“中國式家長”所面對的種種焦慮縮影,試圖探索出一條符合當(dāng)下轉(zhuǎn)型時代現(xiàn)實的中國家庭教育展現(xiàn)當(dāng)代中國民眾精神生活的新路徑。
一 “無根”狀態(tài)下的生存焦慮
20世紀(jì)80年代,隨著改革開放進(jìn)程的加快,經(jīng)濟(jì)迅猛發(fā)展,城鄉(xiāng)之間的差距也進(jìn)一步拉大。體制壁壘的打破為農(nóng)民進(jìn)城提供了可能,而城鄉(xiāng)之間的巨大差異則成為了最原始、最直接的驅(qū)動力。從鄉(xiāng)村進(jìn)入城市、從農(nóng)業(yè)人口轉(zhuǎn)為非農(nóng)業(yè)人口被看作是一次巨大的人生飛躍。由此,城鄉(xiāng)遷徙成為了一股時代大潮,無數(shù)農(nóng)民懷揣著“城市”綺夢,從單調(diào)的鄉(xiāng)村走向富麗繁華的城市,去尋求更多的機(jī)會、獲取更多的財富。由于文化、家境的種種限制,農(nóng)民在城市中賴以生存的方法單一,要實現(xiàn)“農(nóng)轉(zhuǎn)非”更是“天時地利人和”缺一不可,通過“招工”,成為一名正式工人是當(dāng)時許多農(nóng)村青年的共同追求,農(nóng)村女性更是以嫁給正式工人為榮,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穩(wěn)定和體面,更意味著可以以“工人家屬”身份進(jìn)城,獲取成為“城里人”的機(jī)會。《家長》中的王國慧便是一名惹人艷羨的“工人家屬”,她的丈夫何懷禮在城里的煤礦工作,煤礦出臺了新政策,讓王國慧和兒子把戶口遷到了礦上,搖身一變成了“城里人”。村里人陡然對她生出了許多羨慕與尊重。而小說的后半部分,農(nóng)村姑娘麻玉華以嫁給王國慧的傻兒子為籌碼來獲得城市戶口,更加說明了在轉(zhuǎn)型時代下“城里人”對農(nóng)民群體的巨大誘惑。
但擁有了城市戶口,并不意味著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“城里人”。人是社會的動物,無時無刻不處在與社會的交往之中。戶口身份的轉(zhuǎn)變只是一個門檻,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,更重要的是縮小乃至消弭城鄉(xiāng)之間的文化與習(xí)慣差異,獲得他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身份的認(rèn)同。否則,戶口的轉(zhuǎn)變永遠(yuǎn)只是形式上的變化,而這一群體則會始終處于既無法融入城市,又不甘心回到農(nóng)村的精神“無根”的生存狀態(tài)。王國慧剛進(jìn)城時,“城市生存法則”使她無所適從,兒子何新成上學(xué)的事情教會了她“拿人民幣開路”;嚴(yán)格的計劃生育規(guī)定,又讓她失去了第二個孩子。值得注意的是,這個“失去的孩子”如同隱喻:流產(chǎn)之后的王國慧得到了在居委會抓計劃生育的工作,從“承受者”變?yōu)椤皥?zhí)行者”,繼而成為了一個小小的“領(lǐng)導(dǎo)”,從最初進(jìn)城時受到輕視,到以一個“城市人”的身份去為兒子“挑選”農(nóng)村妻子——“失去的孩子”恰恰是她拋棄農(nóng)村印記,接受城市文化與隱性法則的開始。自此,她身上開始帶有了城市人的狡黠與精明,開始懂得如何在這座城市中“扎根”,如何真正地被這座城市接受。農(nóng)民群體從鄉(xiāng)村融入城市的過程中,也包含著鄉(xiāng)土觀念、傳統(tǒng)道德與城市文化的激烈碰撞,尤其體現(xiàn)在對“性”的重新認(rèn)知與接受上。王國慧的轉(zhuǎn)變是有限度的,她始終保持著傳統(tǒng)鄉(xiāng)土女性的保守與持重,而在城市文化中浸染了更久的何懷禮顯然有著更為開放的“性觀念”:妻兒進(jìn)城之前,他孤身一人在礦區(qū)生活,井下繁重?zé)o趣的工作、如影隨形的死亡威脅,激發(fā)了男性的本能欲望,與千千萬萬的單身打工者一樣當(dāng)代中國家庭教育現(xiàn)狀,他急需獲得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慰藉,于是他開始背著王國慧“采野花”,以此作為生活的調(diào)劑。也正因如此,當(dāng)在外打工的老五和宋嬌娥來礦上家里借宿時,王國慧表現(xiàn)出對不道德“茍合”行為的厭惡與鄙夷,何懷禮表現(xiàn)出的卻是司空見慣,是心照不宣。“性”的漂泊與放縱,在某種意義上正代表著轉(zhuǎn)型時代的遷徙群體無處安放的身體與靈魂。陌生而新鮮的城市向他們張開了懷抱,他們卻發(fā)現(xiàn),以往的鄉(xiāng)土生活經(jīng)驗無法為他們提供立足的支點,“本能”的釋放,成為了緩解“無根”狀態(tài)帶來的生存焦慮的一種無奈方式。
二 “暗疾型”家庭的教育焦慮
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、城市化和工業(yè)化的不斷推進(jìn),使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加大,帶動了教育的發(fā)展,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。應(yīng)試教育得到廣泛推行的大背景下,在一定時期內(nèi),學(xué)習(xí)成績成為了區(qū)分“好學(xué)生”與“壞學(xué)生”的唯一標(biāo)準(zhǔn)。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的迫切心愿,以及在人際關(guān)系中產(chǎn)生的攀比心理,使得中國家長們無比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,常常因此陷入一種狹隘的“教育焦慮”。對于底層社會群體而言,經(jīng)過重重考試,接受優(yōu)質(zhì)高等教育,無疑是獲得更好的生存資源、突破階層固化的有效途徑,但受到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,家長們常常會懷抱過高的教育期待,采取不科學(xué)的教育方法。曾經(jīng)引起社會熱議的“虎媽狼爸”式教育,往往會給孩子帶來不可逆轉(zhuǎn)的傷害。再者,底層世界的生存壓力,導(dǎo)致許多家長無暇顧及孩子的教育問題,或是父母雙方都對孩子疏于管教,或是父母中工作較為輕松的一方全權(quán)負(fù)責(zé)孩子的教育問題,這種“父母缺位、不到位教育”會給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難以彌補(bǔ)的缺陷。
劉慶邦在《家長》中想要展現(xiàn)給讀者的,正是底層社會家庭所面臨的教育焦慮問題。丈夫何懷禮在城里的煤礦工作,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王國慧其實是這個家庭真正的“家長”。自身受過的教育、愛面子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,使她竭力維持著家庭各方面關(guān)系的和諧,但事與愿違,這個看似平常的家庭似乎始終被一種無處捉摸的“別扭”氣氛所圍繞,最終還是走向了既定的悲劇結(jié)局。小說一開始就告訴讀者:“王國慧有肝,有膽,膽囊里還有一塊石頭。”這塊膽結(jié)石恰如這種“別扭”生活的象征,它很難被取出,不疼的時候就安安靜靜地蟄伏在膽囊中,一旦發(fā)作卻又威力十足,因而王國慧不得不小心翼翼,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,以免引發(fā)病痛。正如王國慧的家庭,看似和和美美,運(yùn)轉(zhuǎn)一切正常,然而背后早已經(jīng)是“一地雞毛”。丈夫?qū)鹤拥慕逃龓捉谌鍪植还埽€要背著王國慧“偷腥”;兒子何新成在王國慧的控制、父親的不良影響和同學(xué)的捉弄之下,從“三好學(xué)生”變得瘋瘋癲癲當(dāng)代中國家庭教育現(xiàn)狀,王國慧的美好理想終究敵不過冰冷蕪雜的現(xiàn)實。可以說,王國慧多年以來苦心經(jīng)營的,是典型的“暗疾型”家庭,是一種當(dāng)下并不少見的畸形家庭模式。處于家庭中心,努力讓家庭保持運(yùn)轉(zhuǎn)的“家長”王國慧,不得不應(yīng)付著來自各方的壓力,她無時無刻不處于無處捉摸又無處不在的“焦慮”之中。
對于王國慧而言,“教育焦慮”只是一種相對集中的顯現(xiàn)形式,“焦慮”產(chǎn)生的根源并不在兒子何新成身上。作為家里最不受重視的小女兒,在血緣維系的親情之外,王國慧和母親的關(guān)系有些過分客氣,甚至冷淡。王國慧的出生是母親始料未及的,甚至動過將她送人的念頭,而母親說出的應(yīng)該一生下來就將她“摁進(jìn)尿罐子里淹死”的氣話,幾乎給王國慧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陰影。再者,王國慧從小就愛學(xué)習(xí),但農(nóng)村傳統(tǒng)的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的理念,讓她上完初中便不得不輟學(xué),這些年來,她無法消解對母親阻止她繼續(xù)學(xué)業(yè)的怨氣。或許正因如此,王國慧身上有一股子“傲勁兒”,她把自尊和面子看得十分重要,想在母親面前掙一份“面子”的念頭多年來揮之不去。
以上種種,導(dǎo)致王國慧與母親之間總存在著一層隔膜。可悲的是,她無數(shù)次想避免將這種相處模式嵌套在兒子身上,嘗試以一種更為民主、平和的方式與兒子對話,卻都以失敗告終。在夫妻關(guān)系中,王國慧與丈夫看似恩愛,實則缺乏足夠的、平等的溝通交流。何懷禮在煤礦打工,長期處于工作繁重、異性“缺席”的生存狀態(tài)之中,無法抑制的欲望折磨,使他最終選擇以嫖娼的方式紓解苦悶。如果說何懷禮最初的“墮落”是生理性需求,尚可理解,那么當(dāng)王國慧和兒子到礦上來與他團(tuán)聚之后,他依舊瞞著妻子,將情人帶到家里“偷腥”,便是不道德的、自私的、不負(fù)責(zé)任的。小說中,王國慧兩次拒絕了“性與權(quán)”的誘惑,并不是因為對丈夫的忠貞,而是出于對兒子的愛;面對丈夫的不忠,王國慧也只是在大鬧一場之后,為了兒子的成長,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,想方設(shè)法維護(hù)家庭穩(wěn)定和幸福。在表層和諧之下,王國慧的家庭已經(jīng)是暗流涌動,甚至千瘡百孔。這樣的“暗疾型”家庭,在當(dāng)下并不是個案。
王國慧與兒子之間的關(guān)系,則是小說所要表現(xiàn)的重點,“暗疾型”家庭教育模式的弊端在此展露無遺。王國慧無比重視對兒子何新成的教育,她希望兒子可以考上大學(xué),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,這可以說是千千萬萬個中國家長的共同心愿。丈夫?qū)鹤拥慕逃侵苯哟直┑模饔檬欠疵娴模斯靼艚逃猓€在“性問題”上給兒子做出了錯誤的示范,甚至引導(dǎo)兒子撒謊。丈夫?qū)鹤咏逃暮鲆暎屚鯂鄄捎昧藥捉凇皢逝际接齼骸钡慕逃绞剑瑩?dān)起了“家長”的重?fù)?dān)。她將自己未圓的“求學(xué)夢”寄托在兒子身上,要兒子給她增光添彩,因此她表現(xiàn)出極強(qiáng)的控制欲,無論是在學(xué)習(xí)還是生活上,她都要替兒子濾除雜質(zhì),將自己的意愿強(qiáng)加在兒子身上。她刻意營造出一種虛假的。民主”,以“談話”作為教育兒子的武器,不去了解兒子的真實想法與心理需求,卻引發(fā)了兒子的厭惡與叛逆,效果適得其反。她認(rèn)為嚴(yán)美云作風(fēng)有問題,所以不讓何新成與嚴(yán)美云的兒子來往,使兒子失去了朋友;何新成喜歡上周麗娟時,王國慧以強(qiáng)硬手段加以干涉,在兒子身上埋下了悲劇的種子;何新成瘋癲失智之后,王國慧東奔西跑尋求治病之法,最終卻采取了“沖喜”這樣荒唐的方式,反而將兩面三刀的麻玉華帶進(jìn)家門,這個家庭的悲劇在此時達(dá)到了頂峰,正如最后一章的標(biāo)題所言:“一切都完了”……我們不能否認(rèn),王國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親,但她卻很難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母親,而王國慧式的焦慮與悲劇,似乎每天都在上演,劉慶邦在小說中所表現(xiàn)的,正是他對現(xiàn)實的關(guān)照與深切反思。
三 書寫焦慮背后的人文關(guān)懷
現(xiàn)代城市生活的繁華與富庶,吸引著大量的農(nóng)民走出鄉(xiāng)土,尋找更為理想的生活。而城市既開放又排外的雙重性,使得這一群體不得不想方設(shè)法在罅隙中安身立命,以螻蟻之力對抗冷漠殘酷的城市法則。在此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(xiàn)了一系列問題,這是當(dāng)下中國社會無法忽略一大現(xiàn)實。因此,許許多多的作家將目光對準(zhǔn)了這些“出走的農(nóng)民”,去探尋他們的生存現(xiàn)狀與心靈困惑。對底層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悲歡離合的反映,已經(jīng)成為當(dāng)代小說創(chuàng)作中的一個常見主題。而劉慶邦的《家長》,通過對轉(zhuǎn)型時代中一個底層家庭命運(yùn)的書寫,展現(xiàn)了一位普通家長在瑣碎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焦慮與嚴(yán)峻的教育問題。小說中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,沒有惡勢力的干擾與阻撓,卻無奈地走向了既定的悲劇命運(yùn)。
在一次采訪中,談及《家長》的創(chuàng)作,劉慶邦提到:“家長是可愛的,可敬的,也是可憐的,可悲的,可憎的。寫家長,也就是在寫普遍的人性。”小說中,何家人吃春韭菜盒子的細(xì)節(jié)值得玩味,王國慧在廚房烙,丈夫和兒子在外面吃,她卻一口也沒有吃到:“她就是這樣,凡是兒子和丈夫喜歡吃的東西,她都盡量緊著他們吃當(dāng)代中國家庭教育現(xiàn)狀,自己寧可不吃,一口不嘗。”王國慧在家庭中的狀態(tài),正代表著許多中國式底層家庭的典型情形,打工的丈夫在外忙于事業(yè),孩子為學(xué)業(yè)苦苦掙扎,而家庭成員中為母為妻的一方,似乎總是心甘情愿地付出,在操心全家衣食住行的同時,也要承擔(dān)教育孩子的壓力,卻常常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我們不能忽略,小說中的王國慧在承擔(dān)“家長”這一家庭角色功能之外,還是一個女性,一個獨立的個體,她應(yīng)當(dāng)有“屬于自己的生活”。當(dāng)她把家庭和孩子看作自己唯一重要的人生任務(wù),將全部的心血傾注在兒子身上,勢必會失去自我,也會給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,極易釀成悲劇。什么樣的教育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?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物,作為家長,應(yīng)當(dāng)真正尊重孩子的意志,尊重孩子身心的自由發(fā)展,在孩子的心理出現(xiàn)問題時,進(jìn)行及時有效的引導(dǎo)。同時,重視家庭教育的完整性與示范性,父母應(yīng)當(dāng)對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做出正確定位,并規(guī)范自身的行為,以身作則,為孩子提供良好榜樣。對當(dāng)下家庭教育問題的反思,正體現(xiàn)出劉慶邦這位有著高度社會責(zé)任感的作家深切的人文關(guān)懷。
“作者的可愛之處在于,即使寫了慘不忍睹的一面,亦不忘人性的閃光。他感懷于良知的發(fā)現(xiàn),所以在悲劇的地方,也能生出飄香的花草,讓美的氣息在此流動,那是唯有大愛的人才有的情懷。”盡管劉慶邦在《家長》中書寫的,是一個在當(dāng)下社會極具代表性的悲劇故事,但他依舊保持著對美好生活的希冀、對美好人性的執(zhí)著追求。盡管王國慧的家庭一地雞毛,但她始終樂觀堅強(qiáng),保持著對生活的希望:兒子瘋了,丈夫何懷禮撒手不管,將責(zé)任都推給她;而作為母親的王國慧從未放棄為兒子營造一個美好未來,為兒子“騙”到了一個媳婦兒,給何家留下了小孫子生生,留下了“根”。
“根是什么,根是血脈,根是生命延續(xù)的根本,根是人生的希望。有根在,他們家就會繼續(xù)生根,發(fā)芽,開花,結(jié)果,一代接一代延續(xù)下去。”
小孫子生生是何家的新生,在悲劇幕后,給王國慧留下了一縷希望之光,是她新的精神寄托。這樣的情節(jié)設(shè)置,是給予“王國慧們”的精神安慰,也告訴讀者,生活依舊是值得熱愛的,體現(xiàn)出劉慶邦的悲憫之心與人道主義追求。
作為優(yōu)秀文學(xué)作品的《家長》,不僅揭示的問題發(fā)人深思,而且小說形式、語言、結(jié)構(gòu)、人物形象都具有極高的藝術(shù)魅力。尤其是小說的語言,特別符合人物性格,特別接地氣,貼著心窩行走,有的直戳向當(dāng)代中國“家長”心中的痛點與情感的淚點,顯現(xiàn)出了劉慶邦洞察世態(tài)人情、精心錘煉語言的深厚藝術(shù)功力和自覺的藝術(shù)追求。事實上,新世紀(jì)中國已經(jīng)發(fā)生、正在發(fā)生著巨大的社會劇變,教育問題則再一次成為當(dāng)代中國社會關(guān)注的中心和焦點,劉慶邦長篇新作《家長》所呈現(xiàn)的問題、焦慮、內(nèi)心疼痛與希望,將是一個長期的存在。我們只有直面問題,揭示問題,才有可能尋覓到新的希望,才能夠不重蹈覆轍。因此,如何走好轉(zhuǎn)型時代下的新世紀(jì)中國教育之路,如何解決當(dāng)代中國家庭的種種焦慮,則是劉慶邦留給讀者和社會的更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免責(zé)聲明:本文系轉(zhuǎn)載,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;旨在傳遞信息,不代表本站的觀點和立場和對其真實性負(fù)責(zé)。如需轉(zhuǎn)載,請聯(lián)系原作者。如果來源標(biāo)注有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(quán)益或者其他問題不想在本站發(fā)布,來信即刪。
聲明: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(nèi)容,如無特殊說明或標(biāo)注,均為采集網(wǎng)絡(luò)資源。如若本站內(nèi)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(quán)益,可聯(lián)系本站刪除。